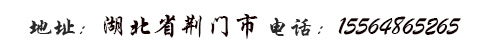故乡的柑橘
|
最近的热点是两个女人,一个拴铁链,一个戴金牌,异常魔幻。除此之外,因为神兽们开学时间再次推迟,深圳地区的家长们哀嚎遍野。不过几家欢喜几家愁,最近也有那么一小撮求财心切的群众在积极研究深圳湾赏金地图,看有无机会通过随手举报从香港来的偷渡客而成为百万富翁。昔日大逃港,今日大逃港,不胜唏嘘。 刀姐大体上属于哀嚎的那一拨。为了防范接下来可能会走偏的疫情,咱还是响应商务部去年11月份的号召,囤点东西先。于是请教了远在西安颇有居家隔离经验的魏导,草拟了囤货清单。顺便学习了著名的抗疫蔬菜七兄弟:大白菜,白萝卜,红萝卜,土豆,洋葱,西葫芦和卷心菜;米也再囤个40斤;水果的话看推荐囤的是苹果、柑橘这一类。 根据本人儿时的经验,柑橘只要保存得当(即给每个果子都套上个小塑料袋),从秋季吃到过年完全没问题。所谓柑橘,除了桔子(蜜桔)之外,还包括柚子、甜橙、抛(音)柑、桔红、篮桔等等。那时我家有柚子、篮桔、抛柑树各一棵,种在房前屋后;还有桔子树若干,分布在菜园菜地。 当时我们那儿白心柚子树更常见,而我家那棵是红心的。于是老爸坚定地认为那是一棵沙田柚。后来可能是因为房屋重新翻盖,那棵沙田柚子树被砍掉了。再后来老爸又补种了一棵白心柚子树。补种的这棵不是什么名头大的品种,就是一棵别人家的味道还不错的柚子树底下的小树苗挖过来给种上了,年年结果到现在。前年回家发现都正月了那树上竟还挂着不少黄皮柚子,如同一只只灯笼。而且树底下掉的也不少,无人拣拾。而我那棵柚子树离路边真不远。尽管慎重地参考了“王戎不取道旁李”的典故,我还是拿竹竿从树上戳下来几个给灯灯玩。出于好奇也吃了一个,有点干,还行吧。 小时候我奶奶家菜园里的桔子树比较多,估计有十几棵,但每棵树上结的桔子味道差别不大,而且基本都是有核的。因为没有核的桔子那时会被单独称为“无核桔”。其中有两三株成熟得最早,干脆就被叫做“早熟”。早熟能吃的时候,最早也在国庆节了,据说那个早熟的品种就叫“国庆一号”。 到了国庆节前后,我跟我的堂姐妹们就已经开始对奶奶家菜园子里的青桔子们垂涎欲滴了。而且我们对哪棵树上的桔子先熟了然于胸。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每次都是那棵挨叔叔家菜园的树先熟。到了准备摘桔子吃的“那天”,现在回想起,“那天”是一个既没有准确的日期,也没有真诚的约定一天,就是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阳光明媚的周末。可能是吃完午饭后不久,心中馋虫一动,自言自语道:搞两个桔子七可。到了菜园子里,东瞅西看,四处打量,找到那棵树向阳的地方,挑那些绿色最浅又泛点黄的青桔子,轻轻松松揪下来。那就一定是一个能吃且将将能吃的桔子了。这种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桔子,表皮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一剥开,满手都是黄绿色的桔皮油。但桔皮的内侧则白生生的正好用来擦手。包括桔瓣上的白色筋络,在撕下的同时也能顺便擦下手。 最开始的一两个桔子总是会细细地品。而吃桔子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首先将剥去青皮的桔子分成两半,再掰开其中一瓣,用牙齿咬开一个小口,然后用两手把桔瓣的皮分开,这时颗粒分明、晶莹剔透的桔肉就会展露在眼前。一口吃下,还带着太阳热度的桔汁瞬间充盈口腔。刚入口主要是酸,过会儿又有回甘,中华小当家的光芒瞬间打开。等吃到后面人就懒了,桔瓣的皮就不剥了,直接吃。这样因为桔瓣外面的白色筋络得到保留,反而能中和青桔子的酸味。 据我观察,有些大人吃桔子时更会偷懒,他们会直接连青皮将桔子分为两半,然后一瓣一瓣掰着吃,吃完桔子的青皮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小孩几乎没有这样吃的,可能因为力气不够大?刚成熟的桔子是不能多吃的。因为等到吃饭的时候就会发现牙早已酸倒了。 除普通桔子外,篮桔也挺好吃的。其实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篮桔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因为实在少见。篮桔的个头比普通的桔子小得多,只比砂糖桔略大,但是核跟普通的桔子又差不多大,因此显得果肉很少。篮桔成熟后颜呈亮橙色,整体有点像迷你版的沃柑但它的味道更浓郁又独特,有点像榴莲里的甲仑。不过篮桔的味道受年份影响比较大,有的年份特别美味,有的年份又味同嚼蜡。最近几年可能是因为树龄老了,采光又受限,据说味道很一般了。桔子的味道跟光照关系非常大,即便长在同一棵树上的桔子,位置不同味道也是千差万别。那种长在树底下的,常年不见阳光的桔子即便最后在树上熟了,味道也很难再回归。 味道不怎么样的还有另外一种偏橙子形态的柑橘叫做“抛柑”。“抛”是常德方言,形容词,大意就是蓬松不紧实,用来形容抛柑本身也算很贴切了。因为抛柑的果肉组织松散,水分极大,也极酸,酸中还带苦,苦得有点像西柚,一般人很难完整的吃完一个,除了我姑姑。据说她曾跟人打赌连吃十个且轻松取胜。不过抛柑树的叶子能用来当调料去腥,也算是天生我材了。 抛柑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大小颜色跟它极其类似但是果肉更紧实,名字就叫“紧柑”。相比抛柑,紧柑的口感会好一些,它几乎没有抛柑的苦味,又把抛柑的甜度增加了一些,仿佛上帝在调参数。把紧柑再调甜一点,紧柑就变成了“桔红”。桔红的味道就有点像橙子了,但又不像橙子似的只有甜。那会儿某小学同学家有桔红树,带到学校我偶尔吃过,吃完内心直呼yyds,一度幻想拿我家的抛柑树去换。桔红再调甜就成甜橙了,那时的甜橙好像就一个品种,小小的,甜度很高,但美则美矣,毫无灵魂。 紧柑和桔红都是把抛柑的味道往好的方向调,如果反过来,那抛柑就成了另一种名字低到尘埃里的柑桔:“蠢坨柑”。不过蠢坨柑也算名副其实了,它气味恶臭,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到了拿完之后都要洗手几遍的地步,简直是柑橘之耻。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能得以存活且拥有姓名,难道是一味中药? 写到这里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不过周五跟DL聊的时候还想起来一件关于桔子的旧事。多年前,我跟同学在上小学的路上,刚剥完桔子准备吃的时候,路过了一个池塘。然后我俩突发奇想,想知道剥了皮的桔子扔到水里会不会浮上来?于是我们松开手让桔子掉了下去,一开始没动静,我们觉得桔子可能是沉下去了,可不一会儿,那个桔子竟然奇迹般地浮了上来。我俩开心之余自以为通过科学实验掌握了一条规律,于是想重复实验结果就将桔子举得高高的再次让它掉到水里。结果这次等了很久很久,桔子再没有浮上来。当时的感觉就是:生活啊,你欺骗了我。难道因为我们举得太高导致桔子直接陷到淤泥里去了吗?到现在仍是未解之谜。 刚才索性剥了一个沃柑放到水里看看,发现它既没有沉到底也没有浮上来,而是稳稳地悬浮在水中靠下的位置,挺有意思。与之相对的,没有剥皮的沃柑则轻轻地浮在水面上。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如果想借助柑橘偷渡的话记得千万不要剥皮。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ngpihea.com/hphpk/10530.html
- 上一篇文章: 生椰月销量超万杯椰子全国断货,
- 下一篇文章: 板栗的功效与作用,板栗怎么做才好吃又简单